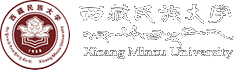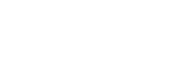魏景波开场就为听讲师生科普了杨柳的生态习性和文化习俗,指出杨柳起源于中国,适应性较强,即所谓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整场讲座从“杨柳异同与杨柳并称”、“古诗词中的杨花和柳絮”和“杨柳意象的文化意义”三个方面展开。首先,在古人的文化观念中,“杨”和“柳”就可作为互训或互称的同一种植物,古人并称杨柳,一般专指柳树,而非兼称杨与柳。古诗中的绿杨、垂柳多指垂柳。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”“长安陌上无穷树,唯有垂柳管别离”即是例证。而杨在少数特定场合,如“白杨”意象,可指杨树。李白诗化用《古诗十九首》“白杨多悲风,萧萧愁煞人”便指杨树,其萧瑟之声更显悲凉之意;其次,在古诗词中,杨花、柳花、柳絮与杨絮,皆指柳絮。白居易《别柳枝》“柳老春深日又斜,任他飞向别人家”,李白《金陵酒肆留别》“风吹柳花满店香,吴姬压酒唤客尝”,晏殊《踏莎行》“春风不解禁杨花,濛濛乱扑行人面”等作品,便运用杨花与柳絮等意象进行创作;再次,杨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,有写景、寓情与拟人三大类,一是写景既有早春初柳,又有晚春烟柳,二是常寓相思离别之情,漂泊无依之情,三是通常用来拟写青春女性。
魏景波深入浅出的讲述,为在座师生带来深刻启发——古代文人墨客体物入微,观察细致,通过时代的演进,杨柳衍生出了复杂而多元的“意向群”,其中蕴含的意义彼此关联而又情形各异,值得大家深入了解和把握。
(文、图:姚晓晓/ 审核:王军君)